此外,在长城灵魂摩托车的研发上,我们完全沿用了汽车领域的研发流程,在性能、质量甚至是服务方面,都采用了高端乘用车的标准。
《种子帝国》(Seed Money: Monsanto’s Past and Our Food Future)是俄亥俄州立大学环境历史学教授巴托·J.埃尔莫尔(Bart J. Elmore)的第二本书,2021年于美国出版。“种子帝国”指的正是如今已被拜耳(Bayer)收购的孟山都公司(Monsanto)。这本详细回顾了孟山都发家史的书获得了美国新闻学、环境历史学以及商业历史学三个专业领域的五个年度奖项。《种子帝国》实至名归。以扎实的学术研究为依托,作者埃尔莫尔既从宏观视角揭示了孟山都对于全球食物体系的影响,又总能在浩如烟海的经验材料中体会到人物的细腻情感,拆解出不同事件的脉络和彼此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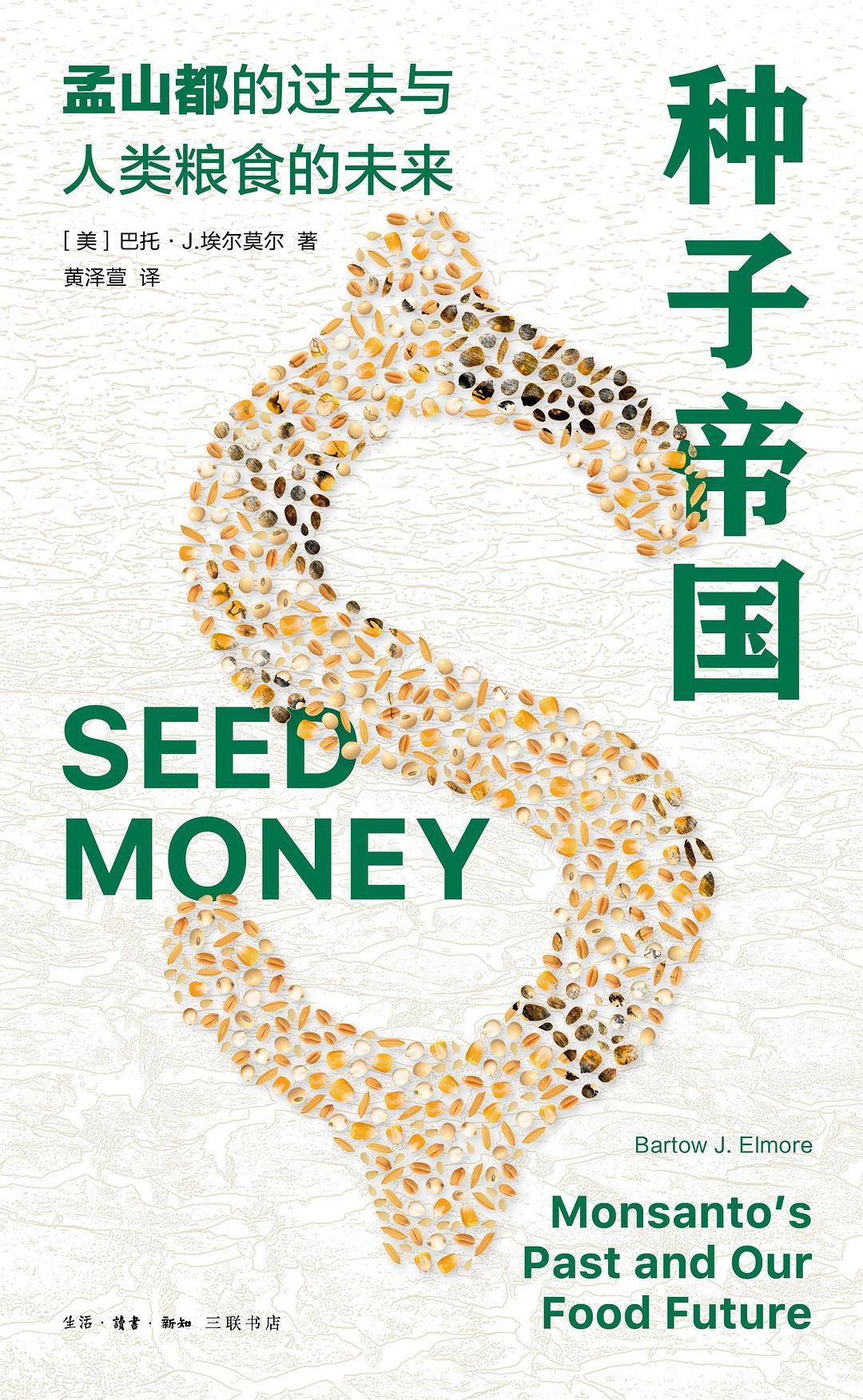
《种子帝国》
该书中译本题目中的“帝国”二字极为传神,揭示出孟山都公司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它以化工企业之底色进军食品加工业、日用品行业、农业生产领域乃至环保行业之后,对这四个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却通过化工和基因技术相互关联起来的领域形成实质控制的过程。尤其在食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领域,“帝国”的控制威力同时作用于生产端和消费端。在生产端,小生产者的独立性被无情剔除,他们被塑造为依赖于孟山都的生产过程的一环。在消费端,人们面对的食品虽然品牌众多、琳琅满目,但恐怕很多食物的背后都盖有孟山都参与制造的印章。
然而,这个帝国是人类的福音么?书中写道:“由于孟山制造的有毒物质的遗留问题,这家公司一直在美国最令人讨厌的公司名单上,一些人把它称为孟撒旦(Monsatan)。”孟山都生产的化工产品给美国乃至全人类带来了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污染和破坏,难以预防或治疗的恶性疾病,以及因污染、疾病和对孟山都模式的依赖而倾家荡产的生计模式。
吊诡的是,深受其害的美国人民一直在状告孟山都,科学家们也一直在揭发孟山都的问题,孟山都却一直没有倒台。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抵抗对孟山都来说,反而成为其砥砺成长的“挫折”。这一逻辑从该书的目录中就可见一斑。该书分为五个部分,每个部分的标题对应着孟山都不同的发展阶段。第四部分的“杂草”比喻那些阻碍孟山都发展的不和谐声音。比如,上诉讨要公道的美国人民,各国环保和农业部门对孟山都产品的质疑等等。然而,第五部分的“丰收”却暗示了孟山都虽历经狂风暴雨却安然无恙的“大团圆”结局。
不过,孟山都的大团圆结局并不意味着人类的粮食生产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种子”“根茎”“植物”“杂草”“丰收”串起了孟山都的发展史,在这一明线之下,我们总能读出另外两条交织在一起的线索。首先,孟山都公司的发展历程正是美国食品加工业和农业发展的缩影,它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推广过程正制造了一种关于食品和农业的意识形态。孟山都历届总裁的个人特点也表征了这一意识形态。第二,为应对美国人民的反对之声,孟山都公司逐步设立了自己成熟的律师团队、科研团队、医疗机构、公共关系也即政治游说团队、种子纠察团队和举报擅自留种的电话热线。本书清晰地剖析了这些公司部门是如何在本质上也属于美国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这些公司部门连同美国的政府部门一道,在巩固了孟山都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同时,也巩固了由进步主义、自由买卖、自由选择权、遵守司法和追求利润等“部件”组成为一体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美国人民的抗争虽取得了部分成功,却总是在美国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框定的范围中兜兜转转。
根据《种子帝国》的梳理,孟山都的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十九世纪末开始,依靠煤炭、石油等原材料,孟山都以糖精、咖啡因等食品添加剂起步,逐步在日用化学品领域获得扩张。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切断了欧洲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运输,为孟山都从欧洲获取化工原材料和化工技术制造了障碍,却也因此“迫使”孟山都的第一代创业者转而开发美国本土原材料,锻炼了自己的化工技术,成功在二战后完成了相对于欧洲石油化工业的“弯道超车”。二十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是孟山都筹谋转型的过渡期,日用化学品产业依靠的煤炭、石油是有限的,但孟山都的逐利扩张是不能停的。1970年,除草剂草甘膦诞生,标志着孟山都进军农业生产领域。事实上,草甘膦的前身橙剂早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越南战争中投入使用,作为武器给越南人民带去了严重的生态灾难。但改头换面了的草甘膦,却成为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向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推广“绿色革命”的主打产品之一。1984年,切斯特菲尔德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建立标志着孟山都公司的发展进入到了第二个阶段。生物技术和化学工业之间的配合是其第二阶段发展的主要动力。孟山都和美国共成长。当孟山都成长为巨型跨国公司的时候,美国也成长为新一代全球霸主。
在《论再生产》中,阿尔都塞揭示了意识形态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在过程上的同一性。在同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扎根于物质性的和实践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没有不借助于意识形态并在意识形态中存在的实践”,也没有不扎根于物质实践,并在物质实践的过程中生产出来的意识形态。在《种子帝国》这本书里,我们能读出意识形态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生产在过程上生动的同一性来,也能看到意识形态是如何借助物质实践而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的。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状告孟山都的故事总是重复着自己的“原型”结构,下一个官司和前一个官司之间总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处不仅包括受害者们的苦痛,还包括了司法流程旷日持久、律师团之间的斗智斗勇、孟山都锲而不舍的政府公关,等等。在一些官司的最后一刻通常会有一个超越了司法范畴的美国政府出场,与孟山都签订协议,挽救孟山都于危难。政府为什么要出场呢?美国不是一个自由、民主、进步的法治国家么?政府不是不应该干预司法和市场的么?
上世纪七十年代,孟山都奈特罗工厂的工人及其家属委托律师考威尔控告奈特罗工厂的生产过程会泄漏有害物质二噁英而危害工人健康。1984年,当孟山都公司的代表律师洛夫在法庭上回应考威尔的时候,他直白地说:
这是一家公司。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赚钱。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洛夫的大实话揭示了美国政府支持孟山都的原因:孟山都发展对美国的发展和扩张有利;孟山都如果因某些问题而倒台,会威胁美国政府的利益。这一点在孟山都经历过的很多难关中都得到了印证。
孟山都的创始人约翰·奎尼就曾有惊无险地渡过了一个难关。支持过《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奎尼原本希望该项法案能为孟山都的产品带来政府许可的广告效果,增加公众对其产品的信任。然而,他等来的却是美国农业部化学局局长哈维·威利依据《纯净食品与药品法》对可口可乐汽水中的食品添加剂的质疑。孟山都每年为可口可乐提供大量的糖精和咖啡因,这两项大额订单支撑着孟山都的发展。面对农业部的猛烈诉讼,法庭上的奎尼如坐针毡。但事情的走向证明奎尼的紧张完全是杞人忧天。
可口可乐和奎尼都不需要证明添加到软饮料中的咖啡因是无害的,因为首席法官爱德华·桑福德从未允许陪审团讨论这个问题。……可口可乐的法律团队在法官席前主张案件应该被驳回,因为原告从未证明咖啡因是被人为“添加”到可口可乐里面的。法官桑福德同意这一观点,最终指示陪审团做出了有利于可口可乐的裁决。在那些指示中,桑福德间接提到了奎尼的证词。他说:“一种天然食品不能被认定为掺假,比如咖啡。虽然一杯咖啡平均的咖啡因含量远高于一杯普通的可口可乐……但里面的咖啡因……是天然和正常进入其配料的基本成分之一。”
桑福德法官、可口可乐的律师团以及孟山都的创始人奎尼一起向我们展示了一场教科书级别的意义接合与拆分游戏。在被告证明添加到可口可乐里面的咖啡因是无害的之前,需要先由原告证明咖啡因是被人为“添加”到可口可乐里面的。而原告没能证明咖啡因是否被“人为添加”,同时,“人为添加”由被告的证人,也即配料提供商奎尼先生解释为“天然和正常进入其配料”。于是,添加添加剂的主体被抹去,添加剂自己“天然和正常”地进入了配料后,可口可乐和孟山都皆大欢喜、顺利过关。这一案件的裁夺真是特别符合法律程序和法律专业的标准。
这样的文字游戏当然一戳就破。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埃文斯·休斯看透了这个判决的荒谬之处,推翻了初审法官桑福德的裁决,重申了“《纯净食品与药品法》的全部意义在于‘保护公众免受有害成分带来的潜在危险’”这一宗旨。虽然“休斯法官将案件发回下级法院,要求陪审团最终应该讨论咖啡因是否真的对人体健康有害。”但是还没等陪审团讨论咖啡因对人体的影响,可口可乐就和政府私下达成了利益交换协议,农业部撤诉,可口可乐减少饮料中的咖啡因含量。
赢得政府的支持是个有效方式,奎尼也开始采用这一方式。面对农业部对糖精的禁令,奎尼和罗斯福总统取得了联系,总统慷慨复信支持了孟山都的糖精,孟山都的律师马上将这封信公之于众,用以证明糖精对健康无害,同时将矛头对准美国政府对食糖的保护性政策。孟山都从三个层面做自我辩护。首先,它指责美国政府保护了糖农,从食糖销售中获取高额税收,却对糖精颁布限制令,剥夺了个人消费者的选择权。孟山都用化学工业制造的糖精为消费者带来了选择的自由,不应被禁止。第二,根据市场自由竞争的原则,美国政府不应助推食糖行业获得垄断地位。第三,糖精对消费者的健康居然有好处:
“这个国家的人民正遭受着食物价值过剩的痛苦,而不是食物价值匮乏的痛苦。”换句话说,糖精对于因补贴和关税而变得暴饮暴食的食品体系来说是一种化学纠正剂。美国人已经吃得很饱了,而化学物质可以帮助他们保持苗条。这是进步时代孟山都给这个世界的信息。
1925年美国农业部终于取消了对糖精的禁令,孟山都的糖精获得了持续生产。糖精对健康到底有怎样的负面影响被转化为“有助于让人摆脱对糖的依赖”,而自由选择、自由贸易等进步观念更是站到了台前为孟山都赢得意识形态战场上的胜利。
“任何意识形态性的观念除非它能贯穿到政治和社会力量的领域,贯穿到不同势力之间利害攸关的斗争之中,都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效应。”奎尼有关添加剂的证词之所以能在法庭上发挥作用,并非因为它迷惑性很强。孟山都围绕糖精建构的支持糖精就是支持健康、自由贸易和自由选择权这一套话语也并非真理。但它们却都树立起来了,发挥了效用。因为它们不仅仅是纸面上的话语表述,而是与特定的社会力量紧密结合在一起。在孟山都的故事里,特定的社会力量是走到一起寻求共同利益的可口可乐公司、美国政府,和孟山都公司,他们在虽旷日持久但回报丰厚的司法和政府公关的实践过程中打造了自由贸易、自由选择、进步健康的生活的意识形态。即便其中一些个别的——诸如美国农业部这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偶然地未能忠于职守地贯彻资本主义谋取暴利的最终目标,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会予以纠正,让事情遵循“(企业)它的存在就是为了赚钱……这就是我们的制度,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中所透露出的原则来发展。
翻开《种子帝国》,我们就会发现,频繁出入法庭对孟山都来说是家常便饭,类似原型结构的故事也还有很多。1970年代,美国分别于1970年和1976年通过并颁布了《国家环境政策法》《资源保护与恢复法》和《有毒物质控制法》。1980年,纽约州北部一个建于有毒废弃物倾倒场旁边的住宅社区发起了草根社会运动,推动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响应、赔偿和责任法》(又称《超级基金法》)。根据这些法律,美国环保署有权追究企业污染者的责任,督促有关公司清理有毒废弃物。看上去,法律在美国人民的抗争和推动下日趋完善,然而,现实却演变为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果。首先,根据法律,既然某块土地已经被孟山都污染了,那么在这块受污染土地上居住、耕作的居民就不可继续使用这块土地了,即便这块土地本就属于他们。同时,环保署不但没有勒令孟山都将污染产业停产,反而把清理土地的任务交给孟山都去做。这恰恰是遵守《超级基金法》的做法:由污染企业负责处理污染。于是,既然土地已被污染,土地的主人不可继续使用土地,必须清理土地,那么孟山都就可以打着处理污染土地的旗号,低价购入已被污染的土地,继续做生产污染品的事了。
美国人民的抵抗起到了效果,新法颁布并被执行,政府部门履行了职责,企业为自己的污染行为付出了代价。但是,社会、政治、法律形成的完美闭环却为孟山都的持续生产打开了方便大门。孟山都的损失是多花了一笔购买土地的钱,但比起停产整改的损失来说,这点损失不算什么。受污染毒害的社区居民似乎也解决了问题,通过卖地搬迁到了别处去。然而,污染却在持续,污染埋下的恶果,终有一天会以更大的量级爆发,影响的范围也将越来越大。
布满全美国的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配合得天衣无缝,促成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继续。同时,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也获得了再生产,通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思考、实践的主体也一并生成。
1990年代,美国环保署发现美国的苏打泉镇处于致病性极高的放射性矿渣的污染中,这些放射性矿渣来源于孟山都工厂的废料。苏打泉的居民们顿时不安起来,希望污染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然而,他们的“自由选择”并不多。居民们可以“减少在地下室的时间……将主要生活区从地下室搬到上层”,但是这个选项治标不治本,受核污染的危险也依然存在。居民们也可以选择“改建、屏蔽或部分清除”炉渣,孟山都则只负责测试和咨询的费用,其余费用需要居民支付,这对于居民们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负担,而且治理过程会对仍生活在当地的居民带来生活上的干扰,事情传出去之后还会连累当地的房价下跌,进一步损害居民们的经济利益。居民也可以继续抗争,要求孟山都停产,但是居民们并未提出这个诉求,因为孟山都为拥有3000人的苏打泉镇提供了大约400个工作岗位。如果孟山都停工,那么意味着400个居民们就会失业。苏打泉的部分居民们甚至还提出了站到孟山都一边,反对环保署的选项,这些居民是包括汉森市长在内的依赖孟山都产业链的小企业主。最终,既不想承担治理成本,也不希望自己的私人财产利益受损的居民们选择了对自己损害似乎是最小的选项:卖地、拿钱、搬离。环保署尽忠职守地把治理的包袱扔给了孟山都,孟山都以最小的代价迎合了各方利益。
苏打泉的居民们在“自由选择”、“民主协商”、“维护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里完成了这一意识形态主体的再生产,没有人也没有机构为公共利益负责,没有人也没有机构超越私有财产的范畴去打破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再生产。
按照类似的剧本,当孟山都向美国农民推销、兜售除草剂及其配套的转基因种子的时候,美国乡土熟人社会中的农业中间商虽然一边知道自己有负于农民兄弟姐妹们的信任,一边还是停不下来地为他们推销孟山都的产品,使美国农民不断加深对孟山都产品的依赖,因为中间商们可以获得的佣金实在太诱人了。于是,农民越来越依赖孟山都的除草剂和转基因种子,越来越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孟山都的广告词“农民应该享有(控制杂草的)选择权”就越体现出其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加入孟山都销售团队和种子纠察队的年轻一代可能不会再背负老一辈中间商那样的道德包袱了,当他们在孟山都给他们提供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的时候,正是他们巩固“农民须依照和孟山都签订的知识产权协议,每年付钱购买孟山都种子,自己留种就是违法”这一观念的时候,也是他们过上高收入、高消费生活方式的时候。依赖于孟山都产业链的汉森市长打心眼里不想在苏打泉的污染问题上站到孟山都的对立面上,他爱人于2006年死于因辐射引起的癌症,他自己也患上了癌症。产业是不能丢的,命是可以不要的。吊诡的是,汉森曾认为,反对环保署的进一步干预是“为生存而奋斗”。在汉森的“为生存而奋斗”这一语境中再次获得生命的主体,是被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塑造的、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召唤的主体,即便那个承载主体的肉身已经身患绝症、命不久矣,资本主义的主体却生生不息。在美国政府以美国纳税人的钱,为孟山都制造的橙剂为越南的环境灾害埋单的同时,孟山都又用橙剂的升级版产品以“打造孟山都全球合作伙伴”的意识形态打造了梦想以小成本控制杂草获得农业丰收的越南农民主体。
《种子帝国》以通俗的笔触揭开这些人物、事件、历史过程中的层层面纱,为我们呈现了孟山都帝国形成过程中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美国人民在美国的法律范畴内对孟山都的斗争仍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范畴内做斗争,对美国的国家机器没有丝毫的损伤股票账户配资,对主体的改造也没有本质上的影响。这才是种子帝国所埋下的种子的本质,也正是《种子帝国》所揭露的问题的本质。